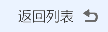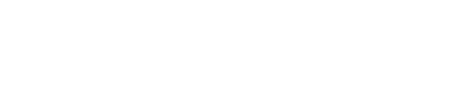隨著社會發(fā)展,村級工業(yè)園產(chǎn)業(yè)低端、土地利用低效、發(fā)展粗放、環(huán)保安全隱患等問題越來越突出。2018年2月,廣東省國土資源廳修訂《廣東省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管理辦法》規(guī)定:對珠三角不再下達普通計劃指標,除原有的省級立項的重大基礎設施外,將原來專項下達給各地的精準扶貧、體育設施、農(nóng)村新產(chǎn)業(yè)新業(yè)態(tài)、農(nóng)民住房等民生設施項目專項用地計劃指標全收回由省級計劃指標統(tǒng)籌保障。這一政策,促使土地資源極度緊缺的珠三角城市加緊推進村級工業(yè)園改造,這對盤活低效產(chǎn)業(yè)用地資源,推動城市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,具有重要的意義,但是,也需要面對村級工業(yè)園改造的4大問題:

1、村級工業(yè)園改造融資比較難
工業(yè)園區(qū)改造需要投入巨額資金,要依靠政府財政資金撬動社會資金參與。目前村級工業(yè)園改造資金來源主要有3種情形:區(qū)或鎮(zhèn)公有資產(chǎn)出資、園區(qū)權(quán)利人出資、非園區(qū)權(quán)利人以贏利為目的參與改造的社會資本。三種資金都存在融資難問題:
1)區(qū)或鎮(zhèn)融資平臺公司以公有資產(chǎn)及其融資參與園區(qū)改造,受財政政策和資金使用性質(zhì)的嚴格限制,難以滿足園區(qū)改造巨大的資金需求。
2)村集體融資,往往因園區(qū)土地建筑欠缺產(chǎn)權(quán)手續(xù)而難以作為抵押質(zhì)押物獲得金融機構(gòu)授信審批;村民對大規(guī)模融資進行園區(qū)改造表決多持猶疑態(tài)度;園區(qū)企業(yè)作為園區(qū)權(quán)利人,受土地廠房租賃期和投資回報的影響,一般也怠于融資改造。
3)企業(yè)實體以贏利為目的參與改造的融資,因項目回收期長、盈利預期不明確、退出補償機制細化不足、園區(qū)土地建筑產(chǎn)權(quán)手續(xù)欠缺難以采取項目融資,民營、外資等企業(yè)融資參與改造的積極性受阻。
2、工業(yè)園區(qū)權(quán)利人的改造意愿偏低問題
工業(yè)園區(qū)權(quán)利人主要包括村集體、村民、園區(qū)內(nèi)企業(yè),村集體是園區(qū)集體土地所有權(quán)人,部分村民是園區(qū)土地的使用權(quán)人以及園區(qū)廠房的業(yè)主,因此,村集體及村民的改造意愿是決定工業(yè)園區(qū)改造得以啟動的關(guān)鍵。客觀來說,政府主導下的園區(qū)改造能提升其市場價值,會為村集體和村民帶來客觀利益,依常理,村集體和村民對政府的改造政策應該會予以積極的支持,但在園區(qū)改造中“政府主動、村集體和村民被動”現(xiàn)象十分普遍,村集體和村民對園區(qū)的改造意愿整體偏低:
1)部分村集體和村民因園區(qū)廠房已在租或使用,收入有保障,因而對園區(qū)改造消極對待,部分村民認為鎮(zhèn)街政府有政治任務,急于改造,因而產(chǎn)生“拖延改造,爭取更多政府補助獎勵”的博弈企圖。
2)不同改造類型對不同權(quán)利人利益回報差異大,村集體和村民對經(jīng)濟效益不確定的“工改工”和無經(jīng)濟效益的“復耕復綠”兩類改造回避甚至抵觸,而“工改商住”模式又與規(guī)劃不符,因而對改造采觀望態(tài)度。
3)由于“三舊”改造對手續(xù)不全的土地和廠房提供了完善手續(xù)的機會,部分村集體對完善手續(xù)心存幻想,而以拖延改造的方式爭取獲得更多補償。
4)部分園區(qū)確實存在升級改造投入大、改造期較長、企業(yè)贏利空檔期流失、回收時間長且存在不確定性問題。
3、村級工業(yè)園區(qū)土地連片整合推進未如預期
將規(guī)模小、土地零碎分散的數(shù)個村級工業(yè)園,整合為連片大地塊園區(qū),利于今后承載大項目,打造發(fā)展大平臺,提高規(guī)模效益,但總體上看,村級工業(yè)園區(qū)土地連片整合推進未如預期:改造預期利益明顯的“混合開發(fā)”式連片整合,項目推進力度相對較大;改造預期利益不明顯“工改工”類的“跨園區(qū)跨村”連片整合不多、“跨區(qū)跨鎮(zhèn)街”的大規(guī)模連片整合尚未有出現(xiàn)。其原因包括:
1)連片整合涉及用地權(quán)屬更復雜,權(quán)利主體更多,利益分配協(xié)調(diào)更難,其中跨行政區(qū)的連片整合還會涉及不同行政區(qū)域之間的GDP分配、用地指標分配、排污指標分配、稅收分擔、整合成本分擔、利益分成等問題。
2)利益激勵政策不明顯,政府核定的土地連片整合成本、補償標準與單個園區(qū)改造相差不大。
3)政策對連片整合缺乏相關(guān)規(guī)則,連片改造路徑未明,部分相鄰園區(qū)用地涉及控規(guī)局部調(diào)整,按照現(xiàn)有政策和規(guī)劃無法整合。
4、村級工業(yè)園區(qū)改造后的管理機制有待創(chuàng)新
在園區(qū)管理上,村級工業(yè)園主要采取傳統(tǒng)園區(qū)管理模式,即村民自治下的村集體管理或由村集體委托物業(yè)公司進行管理,而行政職能部門則依國家法律法規(guī)行使國土、環(huán)保、安全、工商管理等各項行政權(quán),附之以聯(lián)合執(zhí)法或運動式行政執(zhí)法。由于行政執(zhí)法對園區(qū)來說具有外部性,容易導致行政管理部門與村集體和村民關(guān)系的緊張,管理成本高但效果卻未必理想。村級工業(yè)園成功改造后如何重構(gòu)管理體制,是村級工業(yè)園區(qū)改造不容回避的問題。

 收藏我們
收藏我們 在線留言
在線留言 站點地圖
站點地圖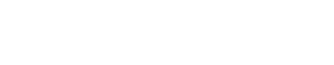
 全國咨詢熱線 :
全國咨詢熱線 :